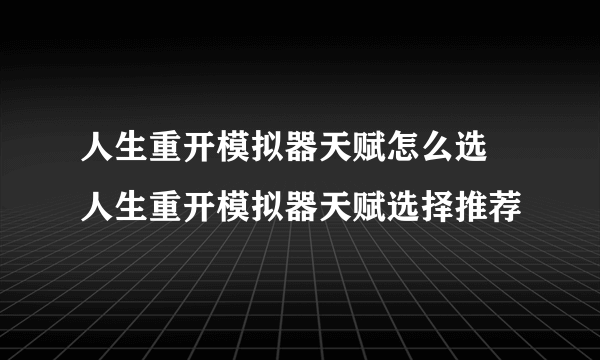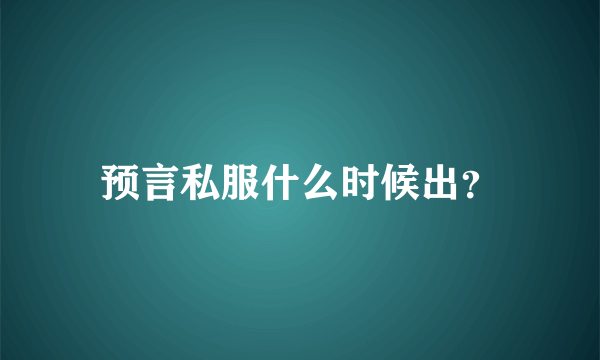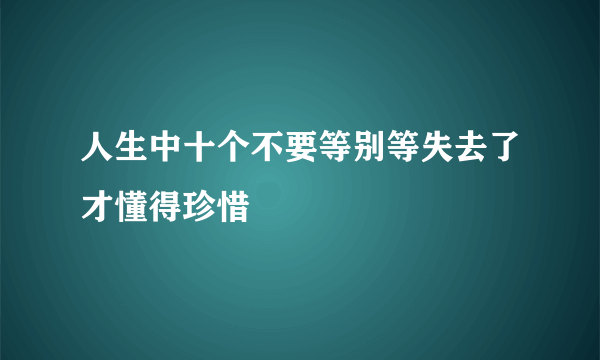《抽卡人生》:一场来自于四年前的抽卡预言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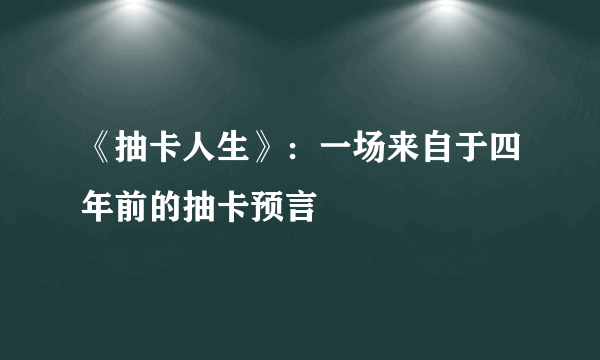
作者:啼书
悠游居,纷杂市井间的一处游戏旅店,欢迎入榻。
本文为游玩《抽卡人生》后的延伸思考和评测。
2020年12月11日,泡泡玛登陆港交所挂牌上市,市值超过1000亿港元——创始人王宁从寂寂无名到泡泡玛特第一家实体店,再到如今主宰“盲盒经济”,花了十二年。
除了集齐一整套系列外,抽到系列中的隐藏款成了收藏者们追捧的大头。
盲盒,成为了“Gacha”踏入三次元纬度的第一步,以五十左右的价格领跑了整个潮玩行业。在盲盒身后,随机口味的花哨汽水糖果与其他后辈正奋力追赶。
游戏,玩具,零食饮料……越来越多的产业被名为“抽卡”的庞然巨物占据,以至于让人遐思: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世界线,我们被Gacha统治?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由抽卡来决定?
但扭蛋机里塞着日常用品和食物,我们还能淡定自若?
在2017年,一款名为《抽卡人生》的手游就早已尝试过,去构架一个抽卡的世界。
求生的囚犯
如果让你来构架一个“抽卡”的乌托邦,你会选取怎样的视点来展现整个世界?
像是传统作品里的公务人员,又或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商家?
《抽卡人生》选取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视点和视角:囚犯。
因为在这个世界中,就连犯罪在监狱里,也只能选择抽卡:抽到吃饭,抽不到饿死。
监狱,往往是一个社会之中,人所能生存下去的下限所在——游戏把主要场景放在这里,将整个世界荒谬的初见展现在玩家眼前。
但这还不够,游戏接下来……留足了让玩家充分挣扎的空间:体力,水份,和精神——玩家赖以生存的三维要素。
在牢狱之中,你每天会获得随机量的配给额度以用来抽卡:从C到SSR的稀有卡,和保证生存三维的资源卡……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卡是什么。
在这款作品中,抽卡不再是玩家的乐趣所在,而是一次次的噩梦——当囚犯一次次地疯狂花光今日份配额却没有得到一张资源卡,当屏幕上代表着角色健康的槽位一点点减少以至于由绿转红,当囚犯一次次迎来疯狂饿死渴死的各式绝望结局……玩家将愈发代入其中,在一次次抽卡中共情角色的绝望。
求生的囚犯,是游戏展现这个世界的视点,也是玩家陷入绝望的起点。
嗜赌的世界
“2419年,在中国由于游戏业的快速恶劣发展,
游戏类型也趋向单一化,并且禁止了引进国外游戏。
用在游戏中的商业模式被用在了社会各个地方:想吃巧克力冰淇淋?对不起,你只能花钱抽食物卡,但有可能抽到香草口味,也有可能抽到草莓口味。
想要买件衣服,试穿完掏钱?不,你需要掏钱去店里抽卡,抽到那一套,才能给你。
因为这样商家可以收获最大的利益,而且能造就更高的GDP。
SSR的概率是1%?
SSR不再是精神享受,而是生存需求。
但在抽满一百张SSR之前,考虑怎么样活下去,显然更加迫切。但即便如此……也避不开高稀有度卡牌的需求。
在监狱黑市中,你需要各类稀有卡来兑换更为珍惜的资源卡,这往往是绝望关头最后的救命稻草。
市场可能是你最后的选择,但需要你积攒足够的稀有卡。
在体力水份见底的最后时间里,你往往只能“梭哈”以求得更多的稀有卡,以换取那最后一口水或是食物——也可能会成为倒数第二口。
但你的san值不会这样轻松放过你,游戏的生存第三维:精神,往往会成为最为致命的拦路虎。
就像是玩家平日里抽到SSR会大呼小叫一样,以SSR和资源卡为救命稻草的囚犯更不用说。但这种精神波动会更为夸张,不同于砸钱吃保底的你,囚犯所面临的是生与死:
抽不到资源卡,精神值便会一点一点滑落。而如果囚犯在陷入疯狂时抽到SSR,则会直接狂乱至死。
许多囚徒都死在了最后时刻的乐极生悲。
精神值的设计,使得《抽卡人生》的表达与体验都区分于其他生存游戏:它将“抽卡”这一行为与癫狂绑定起来,打入了世界观的地基,让玩家重新审视抽卡,重新审视这个嗜赌的世界。
习异而为常
渴死,饿死,癫狂而死,乐极生悲,梦中死亡……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中,“我”熬过了一年,迎来的不是自由的阳光,而是缓刑一年的死刑执行。
疲惫的我似乎看到了制作人笑着描绘自己制作这款游戏的初心:
“整天听到周围人说抽到了这个那个卡很开心,抽到SSR了高兴不已等等,感觉全世界的游戏就剩抽卡了。
然后我想要是未来全变成抽卡游戏了会怎么样……然后一哥们说你干脆做个游戏,里面什么都没有,只有抽卡吧!”
我突然感到有些惊异,因为我已经很难想象没有抽卡的游戏行业了——就像是我现在已经几乎无法想象智能手机被创造之前,人们是怎样生活的那样。
这种惊诧的恍然感,再次出现时,已然是我通关之后:当“我”拿到我的第一百张SSR,走出牢房准备迎接久违的阳光时,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我的身后,是密密麻麻的透明监狱牢房,里面形形色色的囚犯,正在抽卡机前……重复着玩家曾经无意义的轮回。
密密麻麻的囚犯,似乎暗示着那个社会对于异常的习以为常。
退出游戏,我点开群聊,想要分享些什么……却看到了有人在为自己吃舟游保底而哀嚎,有人秀出了自己的“双黄蛋”。
我没再多想,打开CS:GO,抽了几发箱子。